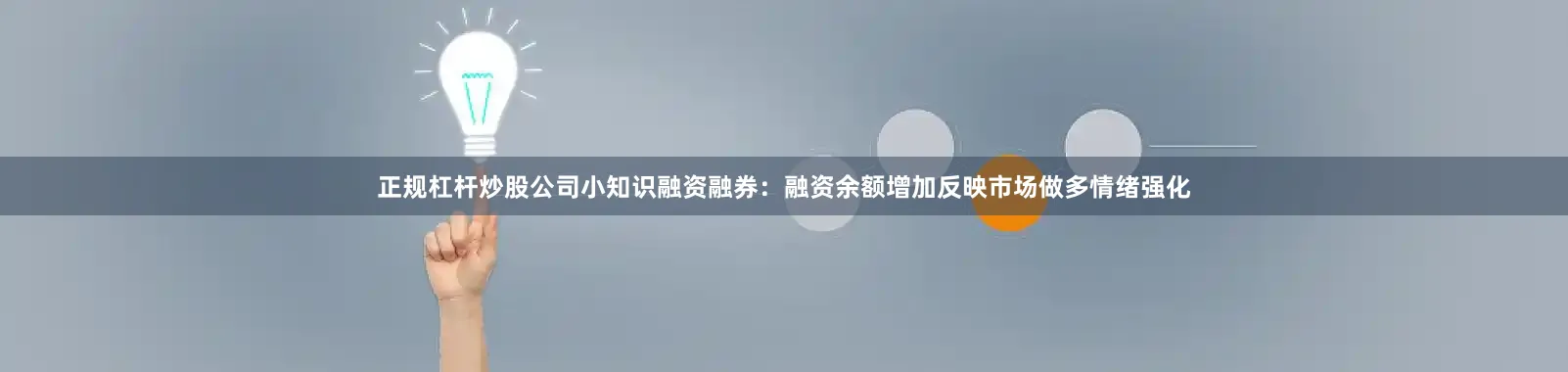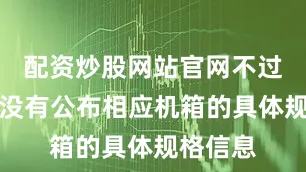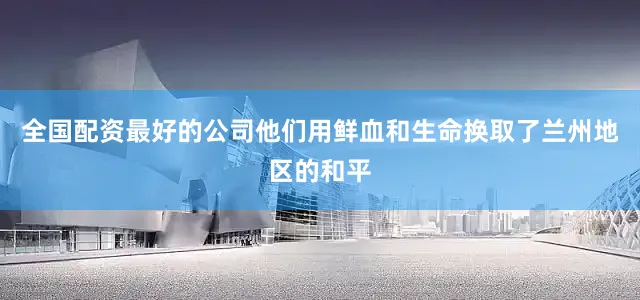当1917年的砖石遇见2025年的晨光,这座哈尔滨百年老街尘封的老商号、1917年由民族资本家毛守和建造的清水红砖小洋楼,如今以“东和昶1917——宽街文化复合体”之名,在主理人宋兴文手中重生。
并非简单的老建筑翻新,而是一场跨越百年历史长河的文明对话——以老楼为“显影液”,开放包容的哈尔滨百年城市基因在巴扬与咖啡香的烟火气中,重新“显影”。
以10个业态的活化实践为“时空折叠术”,
让斑驳的百年老墙与当代艺术展共生,
百年前商贾云集的账簿与怀梦的创业主理人同台
……
散落的历史碎片,
重生为可触摸的“城市记忆共同体”。
7月6日,“东和昶1917”在道里区西十三道街43号全面开放。不仅是一次濒危老建筑解危的成功实践,它更是宋兴文“建筑保护+创新运营”的破题之作——为冰城书写一部多元化投融资、保护传承城市人文历史的“活态历史”样本。
展开剩余94%它也是以宋兴文为代表的
哈尔滨一代城史情怀的主理人
心中的“理想国”:
商业运营与文化使命不再博弈,
而是共同托举一座城市的灵魂与文明基因。
“错构”的“时空折叠术”
“显影”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
当湿版摄影的银盐溶液在“希罗卡雅时光馆”晕开,人们在1904年老巴夺烟庄原址,拍下一张来自19世纪工艺的黑白肖像……
庭院的老榆树下,1948年老电影《哈尔滨之夜》胶片转动,白发观众轻声跟唱;露台爵士夜演的音符,与1926年巴拉斯旅馆留声机的旋律共振……
宋兴文用“更加大胆、有那么点儿离经叛道”,来形容自己当初的构想。东和昶1917项目,被宋兴文视为“老建筑活化利用2.0版本”——作为项目投资人,他从2017年开始集中做老建筑开发,第一个作品是哈尔滨斯大林公园内的江畔餐厅。
今年6月开始,东和昶1917项目的10种业态陆续开放。当多数老建筑改造止步于外观修缮或单一业态植入,东和昶1917以“毛氏旧居”为圆心,用三层空间叙事,织就了一张穿越百年时空的生活网——
宽街博物馆、希罗卡雅时光馆、宽街中古杂货铺、门洞画廊、老俄侨餐厅、宽咖啡酒吧、宽小馆新派哈埠菜创意私厨、宽院花园、宽街民宿、后窗哈派咖啡——10种业态,在使用面积500余平方米的老建筑间,展开“时空折叠”:在希罗卡雅时光馆,人们可以体验湿版、胶片摄影,感受百年前的影像艺术;当19世纪影像工艺与中西餐桌烟火并置,碰撞出的是哈尔滨人舌尖上的中西合璧,“艺术即日常”;在复原百年原生态庭院的露天庭院看一场露天电影,“穿越”百年老街热闹氛围;老门洞里的开放式艺术空间,将集体记忆与历史娱乐生活场景重叠,复活“东方小巴黎”的“夜生活肌理”;爵士舞台、日咖夜酒、咖啡与民宿,让味蕾与居住式沉浸,成为历史叙事的载体……
脱胎于宋兴文此前端街“老俄侨文化复合体”1.0版本,集文博、艺术、餐饮、休闲、住宿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“东和昶1917”,不仅用文化复合体的创新实验做到“复原”,还嵌入了一系列饱满多元的日常元素。
表面上看,10种业态之间,更像是一种碰撞与错构。宋兴文有意制造了一种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碰撞交融。在他看来,西洋音乐与咖啡文化不是“舶来品”,而是冰城百年日常;多元交融非文化断层,而是哈尔滨最珍贵的基因图谱。“就是要利用这样一种‘错构’的生命力,全景再现与呼应中西交融下,哈尔滨百年城市生活与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,让它们重新产生‘心跳’。”
关键是,东和昶1917与国内同类活化项目有着本质差异——复活哈尔滨在中西交融的百年历史长河中“人的生活”,而非“建筑标本”。
复原城市风貌,国内有多种解法。复原百年历史文化名城哈尔滨“人的生活”,对宋兴文来说,几乎无解法可参,“复原生活,比修复建筑更难”。
但至少有一个不需要调研的共识:哈尔滨人曾比上海更早喝咖啡、吃西餐,赏爵士,品西洋绘画……很多人觉得海派文化有情调,而论优雅摩登的文化生活,哈尔滨曾走在全国前列,比肩上海。在宋兴文看来,多元文化正是哈尔滨重要的文化印记,因此哈尔滨百年历史风云下城市生活,是真正体现中国人开放包容的“哈派生活”,也是一种“见过世面”的从容。
在东和昶1917二楼的老俄侨餐厅包房,毛家老屋近百年的老镜子、老梳妆台等老物件,如今都被宋兴文保留在原处。东和昶既是毛守和曾经创建的商号,也是他的住所。这里的一切细节,都成为刻在这座老建筑上的“年轮”。它们见证了一代民族工商业者,在当年外国人主导的街区里创业兴业,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,闯出一片天地。这里承载着哈尔滨民族资本家曾经的创业传奇,也记录下他们中西合璧的生活日常。
因此,东和昶1917绝非单纯的怀旧和复古。“不是为了恢复而恢复。”宋兴文说,“穿越历史的长河,它一直就在它原本应该在的地方——这就是历史。”
如今,人们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,在这里拍老照片、吃俄餐、品咖啡、拍婚纱、办沙龙……走进来、坐下来、住一晚。
这正如宋兴文所期待的:越来越多人走进了这个“历史场景”,真正与老建筑建立起内心上的联系。同时,他们也正成为新的“场景”。
当历史叙事嵌入年轻化的视角和语境,流量正转化为文化认同。东和昶1917为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,打开“五感”,提供一种情绪、一种感受——历史,便更容易触摸。
C位博物馆
历史不再是标本,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呼吸
先有老物件,而后有东和昶1917。
仅32平方米的宽街博物馆,是10个业态中的绝对C位。宋兴文将毕生收藏的百件珍品浓缩于此:1912年哈尔滨首份中文报纸《远东报》发黄的创刊号,记录着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呐喊;从德女中当年的校服,折射出1924年冰城女子教育的破晓之光;哈尔滨最早的华商照相馆“视明馆”拍摄的中国人老照片,记录下百年前普通哈尔滨人的面容与摩登细节;“老巴夺葛万那烟庄”烟标——这件东北首家现代烟厂的证物,与东和昶商号广告信函等百封旧信函、老照片一起,共同编织起宽街百年风云与市井烟火的画卷……
哈尔滨从不缺少媲美全国一线城市的人文历史资产。对老建筑活化利用,宋兴文的底层逻辑始终是,必须基于老建筑本身承载的历史和文化:活化利用,一定要挖掘历史、复原历史,同时保护它的文化性。“唤醒老建筑所承载的城市记忆,唤醒它的灵魂,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实践。”
东和昶1917最大的潜在商业价值,正是它本身蕴含的历史人文。文化的生命力,决定了它的商业的生命力。在宋兴文看来,“博物馆是必须要有的,没有博物馆,没法讲清楚这栋建筑和这条街的历史”。
这座始建于1917年的清水红砖洋楼,所处街道非同寻常。这条始于1902年、全长仅220米的街道,却是中央大街辅街中最宽阔的一条,因而得名“宽街” 。在哈尔滨历史上,宽街创造了多个“第一”:1904年老巴夺兄弟在此创办“葛万那烟庄”,开创东北现代化制烟业先河;1906年哈尔滨第一家中文报纸《远东报》在此诞生;1912年哈尔滨第一家印书售书局“商务印书局”在此开办……上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,宽街更是哈尔滨著名的 “饭店一条街”,先后聚集了几十家中西餐馆,从海成轩、南味馆到五芳斋、福泰楼,再到巴黎饭店、老都一处……南北风味在此交汇,见证了哈尔滨的繁花岁月。
这座小洋楼之于宋兴文,更像是一种“命定的缘分”。此前,它在中央大街几乎默默无闻。宋兴文“入眼”的老建筑,并不在乎名气,看中的是“老”。但最早接手时,发现不仅留下的历史物件少,甚至后人连毛守和的老照片都没留下。
这激发了宋兴文强烈的好奇心。他寻着史料,开始在自己多年来数以万计的历史收藏“悠长隧道”中,展开寻找——几乎没什么难度,他很快寻到了这座小楼的老照片、老物件等诸多历史痕迹。范围不断扩大到整个宽街,“物证”种类多到难以想象,宋兴文拿出来一一精准对应,才发现他手中收藏多年的每一寸历史碎片,都将当年宽街的“高光时刻”娓娓道来。
宽街博物馆是他打造的第二个街道历史博物馆。曾经收藏的无数个“无意间”,如今冥冥之中,成就了今天东和昶1917的C位。
在宽街博物馆内,有一张清末两个中国长辫男子下棋的生活影像照。影像,一直是宋兴文收藏的重要专题。他一直想收集100家华商照相馆,目前已成功找到90多家。在一个旧物网站,他曾看到过一张清末老照片,挂价3000多元。“以往我收来的大部分照片,最高的千八百块。”宋兴文回忆,他记得这张照片至少挂了4年多,一直无人来收。他也曾有过犹豫,觉得有点儿太贵了,但每天日思夜想,最终还是咬咬牙,把它买了下来。
这张照片如今成为宽街博物馆的“镇店宝物之一”:正好与他收集的另一张清末3名女子老照片相得益彰,共同佐证着曾经宽街上蓬勃的影像业。
东和昶1917业态中的希罗卡雅时光馆(视明复古照相馆),对应着1900年初期宽街上的一家照相馆。它是哈尔滨历史上最早的华商照相馆之一,名叫“视明照相馆”。它也是哈尔滨早期商业文化的重要见证。巧合的是,关于这家照相馆的历史,同样可以在宋兴文当年的收藏、如今在宽街博物馆的诸多展品中,有所循迹。
正是无数“命运的巧合”,带给了宋兴文极大信心,令他意识到,“在哈尔滨,没有破解不了的历史,只看是不是真的用心”。
14个老屋组成“理想国”
商业与使命的平衡
宋兴文和这座楼的缘分,始于“一见钟情”。
此前做端街文化复合体,受种种局限,已经没有更多发挥空间。宋兴文便一直将目标锁定百年老街中央大街。
“最开始,是因为我们那会儿每天做核酸检测,这个楼就在检测点旁边。”宋兴文回忆,那会儿天天都能看到这个小楼,彼时它尚未显露真容——被一层黄色涂料覆盖,如同蒙尘的史书,却让他“莫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感”。当时,小楼里住了十几户人家。不到一年时间,宋兴文先后租下3户老屋。当他试图联动整栋楼活化,想说动其他住户,被一口回绝。
2023年11月,专业机构一纸鉴定的D级危房,让先期已经投入大量资金的宋兴文,一时间陷入两难,却也为他带来转机——几个月后,其他业户与他陆续达成协议。尽管成本要翻数倍,宋兴文还是决定放手一搏,引用专业团队,仅不到两个月时间,将D级危房加速解危为B级。
那时候,他天天跟工人们一起泡在施工现场,常常一个人灰头土脸穿梭在“脚手架森林”——在工人们从墙缝间抖出的1917年尘土中,展开一场又一场空间想象的头脑风暴。
那时,宋兴文的脑海中,已经有了一张清晰完整的业态图景。而后,他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想法,在他的“理想国”里,一寸一寸展开实践——神奇的是,东和昶1917如今的模样,与他那个最早出现在脑海中的场景,并无二致。
相比之前的项目,这座老建筑基本是一个完整结构,包括14户老屋在内,总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。它给了一直以来“内心蠢蠢欲动”的宋兴文相当大的发挥空间,也让他“把从前的遗憾与尝试,尽可能发挥出来”。
宋兴文却始终“小心翼翼”——10个业态,全部基于老建筑的原汁原味。“如果是纯商业开发,完全可以把14户老屋打通,因为现有每户也就十几平到三十几平,比较零碎,其实并不好利用。”打通无疑是最轻松、也是最常规的商业逻辑,但“那就不再是老建筑活化利用,而是单纯的商业开发。老建筑活化,不能沿用常规的商业逻辑”。
极致的理想化会与商业盈利存在一定冲突。宋兴文告诉记者,比如东和昶1917目前二楼的包房设置,全景还原了百年前中西合璧的生活全貌,但宋兴文追求得“苛刻”,甚至“不希望二楼是菜味儿,希望更多是咖啡的香气”。为此,他用最大的空间做了最小的容客率。“目前,这里的一切基本是我理想中的样子。”而关于商业盈利,就分阶段来达成,在后续运营中再考虑调整和平衡。
他坦言,很多理想,还是要徐徐图之,在探索中向前。同时,也担心自己被“框定”。
为了更好运营东和昶1917,宋兴文首次采用“主理人共治模式”,引入了摄影师、园艺师、咖啡师、画家、书法家等多位主理人,共同参与经营和分成。这其中,有的是宋兴文承担成本,采用分成机制邀请主理人;有的是邀请主理人带自己的业态过来,自己负责经营,比如后窗哈派咖啡。
在朱敏看来,后窗咖啡能够成为东和昶1917其中一个业态,是“终于有了根与魂”。作为哈尔滨20年历史的本土咖啡品牌代表,朱敏近些年始终专注于从城市人文历史寻找“哈派咖啡”的制作方法与文化起源,因此与宋兴文产生深刻交集。初到这座洋楼,朱敏几乎是“开盲盒”,仅凭斑驳老墙上一面“一见如故”的旧窗,选定了二楼一角的老屋。
作为后窗品牌的东和昶1917分店,定位分明:开启研发哈派咖啡历史的“寻根之旅”。奇妙的是,尽管是独立装修,但最终的陈设风格与美学思想,与东和昶1917整体如出一辙,交相呼应。
在宋兴文眼中,每个主理人有着独立鲜明的个人特质,各有各的想法,各有各的思路。他们都是“有故事的人”,也都“眼里有光”。
东和昶1917,是这一群人心中的“长期主义”,也是他们心中的“理想国”。
城市启示录
冰城“保护性开发”的破题之道
用民间资本活化业态,赋予老建筑可持续生命力,维系城市中人与历史的情感联结——东和昶1917将安全红线、文化底色与商业活水三维咬合,这种模式,正与哈尔滨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新政形成共振:2024年出台的《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实施意见》,明确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租赁、租金抵扣维修成本等方式参与老建筑活化。东和昶1917的活化模式,正成为城市更新的“哈尔滨样本”,为“保护性开发”提供更多方法论。
“很多老建筑,由于历史原因,很多甚至可能只剩下一个立面了,历史遗留很少了。”在宋兴文看来,老建筑越来越少的今天,它的价值一定在于为它重新注入灵魂。在宋兴文眼中,哈尔滨还有不少类似东和昶大楼的宝藏老建筑,以东和昶1917,为这些老建筑提供一个可复制的样板,“未来有机会,还会做更多尝试”。
这个样本的核心价值在于:以文化传承为根基,以商业运营为动力,让历史建筑在现代生活中找到新位置——最好的保护不是让历史成为标本,而是让它继续在人间烟火中生长,成为容纳城市新生活的文化容器。
宋兴文常常一个人站在这座百年庭院的二楼,默默望向楼下,看红砖墙前拍照打卡的人来人往。他知道,当越来越多人在社交媒体分享这里的一切,宽街尘封的记忆,正以一种新的生命方式得以延续。
他向记者透露了“东和昶”这个名字的由来。记得第一次走进这座院落,“当时到处阴湿一片,破败不堪”。这座老建筑当初所开设的商号,最早文献记载的名字叫“东和昌”,后来易名“东和昶”和“东和昇”。沿用中国商号的取名传统,宋兴文最终为这里取名“东和昶1917”,是希望这座穿越百年的老建筑,永远为太阳所照耀。
在他看来,老建筑更像是天文学里的“虫洞”:既可以回到过去,也能去到未来。他想用自己的方式,去对抗消亡。也希望在这座老建筑的“年轮”里,留下“宋兴文的印记”。
他希望百年之后,当哈尔滨人触摸到这座老建筑时,感受到的不仅是穿越百年的砖石,还有这一代人留下的温度——让历史与未来在当下相拥的勇气。
来源:哈尔滨日报
实习生 佟波 记者:王坤/文 韩伟/摄
王坤 石松鹤/视频
责任编辑:田苗
审核:董景峰
发布于:黑龙江省宝利配资-炒股app排名-中国十大正规炒股平台-网上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